近日,南方日报出版社适时推出《唐诗物候》一书,从自然之四季变化及相关节气之顺序的维度,打开了品读唐诗的另一扇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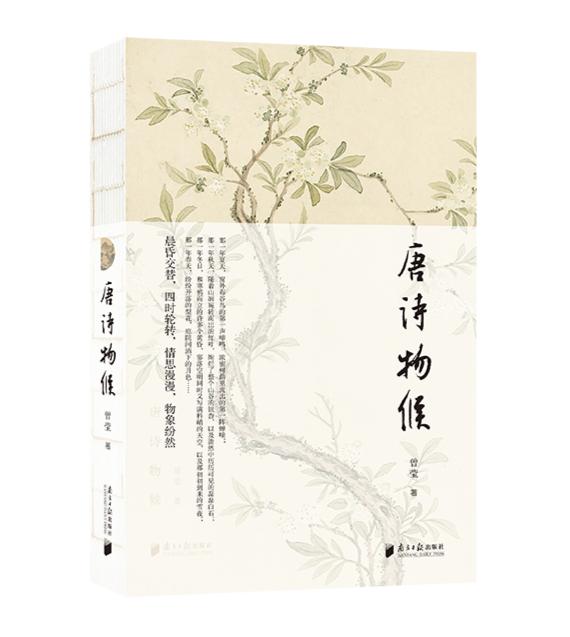
近期,《长安三万里》似乎成了大人孩子必看的电影,票房及口碑持续攀升,再度掀起“唐诗热”。无论是长安的繁华气派、梁园的田园风光、扬州的温柔多姿、塞北的苍凉辽阔,实则都融入在了四季度更迭、万物的感知之中,但作为画面的背景,却往往容易被观众所忽略。《唐诗物候》一书正是立足于此,从节序、物候入手,以四季结构成书,荟萃了百余首描写四季和佳节的唐诗精品,对唐诗展开全面的梳理和观照。
作者简介
曾莹,广东清远人,中山大学文学博士,云南大学文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国古代诗歌、戏曲、元明清文学研究,发表相关论文十余篇。出版专著《文人雅集与诗歌风尚研究初探——从玉山雅集看元末诗风的衍变》(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2011年版)、《畏垒吟卷》(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等多部,点校(民国)杨增新《补过斋文牍初编》(中华书局2019年版)。主持并完成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元代声诗研究”,以“优秀”鉴定结项。另为云南省社科重大项目“云南文学史”子课题负责人。
精彩书摘
引 言
杜牧《李贺集序》里记录了李贺挚友沈子明的一段话,就算隔着重叠的时光读来,也并未减损它的动人:“吾亡友李贺,元和中义爱甚厚,日夕相与起居饮食。贺且死,尝授我生平所著歌诗,离为四编,凡千首。数年来东西南北,良为已失去。今夕醉解,不复得寐,即阅理箧帙,忽得贺诗前所授我者。思理往事,凡与贺话言嬉游,一处所,一物候,一日夕,一觞一饭,显显焉无有忘弃者,不觉出涕。”人生匆匆,太多的光阴与人事都逝去得了无痕迹,似乎就是长林树端的一阵风过,江河湖上的数圈涟漪。然而,当我们回望这令人仓皇无措的匆促时,总有那么一些瞬间让目光有停驻的可能。而这些瞬间,大多都是和物候系在一起的。那一年春天,纷纷开落的梨花,庭院间洒下的月色;那一年夏天,窗外布谷鸟的第一声啼鸣,浓密树荫里流出的第一阵蝉噪;那一年秋天,随着山涧宛转而出的红叶,绚烂了整个山谷的银杏,以及湍然中历历可见的磊磊白石;那一年冬日,和寒鸦而立的许多个黄昏,寥落空明同时又写满料峭的天空,以及那初初到来的雪夜……“一处所,一物候,一日夕”,这样一些细微而寻常的变化瞬息,短暂,却也隽永,仿佛岁月、人生刻度一般的存在,总能有所标记,有所唤醒——这些个总是在刹那间绽放的灵动鲜活,大抵,就是万般虚妄中不易的真实;抑或,是那一切屑屑中最为分明和深长的诗意。
所以,当我们想要有所书写和记录时,总免不了“嗟时序之回斡,叹物候之推移”,目光所向,感触所系,往往都是那些关乎物候的片段、画面。例如简文帝之赋晚春:
望初篁之傍岭,爱新荷之发池。石凭波而倒植,林隐日而横垂。见游鱼之戏藻,听惊鸟之鸣雌。树临流而影动,岩薄暮而云披。既浪激而沙游,亦苔生而径危。
(梁简文帝《晚春赋》)
又像潘岳之题写秋日:
四时忽其代序兮,万物纷以回薄。览花莳之时育兮,察盛衰之所托。感冬索而春敷兮,嗟夏茂而秋落。……庭树摵以洒落兮,劲风戾而吹帷。蝉嘒嘒以寒吟兮,雁飘飘而南飞。天晃朗以弥高兮,日悠阳而浸微。何微阳之短晷,觉凉夜之方永。月曈昽以含光兮,露凄清以凝冷。熠燿粲于阶闼兮,蟋蟀鸣于轩屏。听离鸿之晨吟兮,望流火之余景。
(潘岳《秋兴赋》)
还有陆机写在冬天的字句:
天悠悠而弥高,雾郁郁而四幕。夜绵邈而难终,日晼晚而易落。敷曾云之葳蕤,坠零雪之挥霍。寒冽冽而寖兴,风谡谡而妄作。鸣枯条之泠泠,飞落叶之漠漠。山崆巄以含瘁,川蜲蛇而抱涸。
(陆机《感时赋》)
不知有多少的窗前灯下、湖上江边,也不知有多少的清晓黄昏、白昼长夜,无论是立于庭树,身影寂寥,还是驱车荒野,群山静谧,总会有那么一些喟叹,因物候的推迁而生发;也总会有那么一些时刻,因为这既细微又分明的变化而趋向生动、立体。这样的体会,在唐人的吟诵间有着更为细致和真切的呈现。随意翻开一册唐诗,那些光色声响,便令到昔时的季节流转、晨昏更迭,都一齐跃动于眼前。
最为著名的,当然要数杜审言的那句感叹:“独有宦游人,偏惊物候新。”正因为是宦游在外的人,远离乡原,经受了太多的羁旅漂泊,才会在物候转新的时候,是惊而非喜。万物的苏生,让诗人惊觉的是年光易逝、年岁易老,宦游相伴的种种蹉跎,更令到那些暌违分离、寂寥孤独都变得旷日持久,无从逾越。是以,哪怕眼前是一幅大气浑成、饱含生机的画面,内心的低回、凄惶,似乎都是在所难免的。于是,面对着“云霞出海曙,梅柳渡江春。淑气催黄鸟,晴光转绿”这等明亮、清新的图景,诗人在听到朋友的率先吟唱之后,依然写下了“忽闻歌古调,归思欲沾巾”这样的心绪。这自然是和朋友的共情,但同时也写出了宦游之人共通的心曲。很显然,物候变化对于他们而言,不啻为内心深处的一次次激荡。哪怕是枝头的一枚新叶,林间的一声清啭,都让人不由思索起自身光阴之虚度,生涯之荒废——本应闲适的,偏偏交付给了匆促与琐屑;本应相伴的,却偏偏陷入相隔天涯的形影相吊、岁月暌违。这样的处境,大概最易唤起千年之后,我们内心的那份戚戚然。
当然,留心物候的唐人,并没有限定在宦游的群体。有人惊于物候,自然也就有人耽于物候。与“偏惊物候新”相对,元稹就写过《生春》二十章,充分渲染了有关春天到来的种种物象变化,以及这物象变化引发的色色欣悦。这二十首诗,开头两句有着相同的格式,诗人分明是在切切地追问着,同时也迫不及待地一一作答:
何处生春早?春生云色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漫雪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霁色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曙火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晓禁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江路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野墅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冰岸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柳眼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梅援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鸟思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池榭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稚戏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人意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半睡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晓镜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绮户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老病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客思中。
何处生春早?春生濛雨中。
如此一问一答的张阖,如此长篇累牍的格局,有关春的意绪便纷然洒落在字里行间——细碎着,也堆叠着,回环往复,奔涌不息。整体而言,这一组诗并不见得好,但这些意绪的滋生缠绕却叫人印象深刻,无法拂却。古往今来,那些季节变化的无数刹那,不知可以牵引起多少的心旌摇荡、思绪飘飞。人们每每会在许多不可思议的时刻、场所,感知到那些细微而深长的异样。春天就这么到来了,在每一个飞雪冰岸,每一段细雨初晴。池上水榭,江间舟上,每一次揽镜,每一次凭栏,每一次把盏,每一次倚楼,春天带来的悸动,或大或小,却基本有着鲜明的轮廓,清晰的眉目。而在这样的感知与领受中,诗人似乎也不止直面了春的发生与到来,更看到了属于自己的斑斑心痕。依稀,是朝班之上的肃穆雍容;一转眼,已然是羁旅客愁满腹苦况。仿佛,犹然可见相对时的浓情洽意——“手寒匀面粉,鬟动倚帘风”,儿女绕膝时的天真光景——“乱骑残爆竹,争唾小旋风”。甚至,即使身处老病之中,春的迸发萌动也一般无二;而在半梦半醒之间,同样是与春之气息相傍相偎——“见灯如见雾,闻雨似闻风。开眼犹残梦,抬身便恐融”。而在这样一些物候的纷然、粲然间,唐人笔下的山川岁月顿然有了可触可感的亲切活泼。这些春日里的种种,物象,心情,一时纷至沓来,似乎全然悬停在了我们的脚边、窗前——丝毫不见,任何时空的阻隔。俯仰之间,都是一笔接一笔的真切鲜活。
于是,循着物候进入唐诗的世界,这中间便不再有什么不可逾越的时间。四季的流转,万物的变迁,以及这人世之纷扰代谢,历历鲜明,在在可见,于是也不再有什么今古之间的彻底分别。持卷展读,自是油然而生亲切,也自然加剧了那些相应的所谓会心、所谓懂得。
于唐诗当中,不仅这些物候的影迹随处可见,那些深邃浓炽的情感思绪,纷繁复杂的人物事件,也都有相应的物候作为载体、作为支撑。譬如卢照邻所勾勒的大唐气象,除了大家熟悉的“人歌小岁酒,花舞大唐春”这两句以外,就还有“草色迷三径,风光动四邻。愿得长如此,年年物候新”(《元日述怀》)。诗歌通体焕映着的,就是一副雍容的气度,笃定的神情。而在杜甫笔下,所谓家国的喟叹,亦时常系诸物候之上。如《大历二年九月三十日》一诗,即有:“为客无时了,悲秋向夕终。瘴余夔子国,霜薄楚王宫。草敌虚岚翠,花禁冷叶红。年年小摇落,不与故国同。”某个客居异地的秋日黄昏诗人看着周遭的秋景历历,内心翻涌的,正是常年作客的无奈与伤怀。秋之摇落,映照着心绪的摇落,以及旧日山河的那份摇落。物象各异的描摹铺陈中,的是幽怀难禁。再看老杜另外一首广为人知的作品——“一片花飞减却春,风飘万点正愁人。且看欲尽花经眼,莫厌伤多酒入唇。江上小堂巢翡翠,苑边高冢卧麒麟。细推物理须行乐,何用浮名绊此身。”(《曲江二首》其一)同样是与物候有关,然而清人金圣叹所评却让我们充分感受到寻常物候之外的那份呼之欲出的不寻常。金圣叹写道:
本为万点齐飘,故作此诗,却以曲笔倒追至一片初飞时说起。细思老人眼中,物候惊心,节节寸寸,全与少年相异,真为可悲可痛!
看他接连三句飞花,第一句是初飞,第二句是乱飞,第三句是飞将尽:裁诗从未有如此奇事。
“欲尽花”“伤多酒”,以三字插放句腰,其法亦异。酒是“伤多酒”,入唇最难,本最可厌;而先生叮嘱“莫厌”者,为花是“欲尽花”。看他下“经眼”二字,便将眼前一片一片不算是花,直是老人千金一刻中之一点一点血泪也!
小堂翡翠,不过小鸟,而今日现存,即金碧可喜;高冢麒麟,虽是大官,而今日不在,即黄土沉冥。“巢”字妙,写出加一倍生意;“卧”字妙,写出透一步荒凉。……如此二句十四字中间,凡寓无数悲痛感悟。……
所以,看似是春景,看似在伤春,又何止是春景,何止在伤春而已。
唐人笔下的物候若此,既含蕴深长了那些感喟,也沉淀练濯了所谓辰光。这样的物候书写,真正体现也成就了唐诗的兴象遄飞、鸿朗高华。闻一多先生早就说过,有关唐代诗歌,与其说是唐诗,倒不如说是“诗唐”来的更为恰切。在这样一个诗歌构筑的“绝对”时空里,诗情往往出落得澎湃席卷,同时不失细腻幽深——充溢天地,俯仰皆是。人们面对生活,总是抱持着最大化的热情,也显露出最为饱满、深邃的诗思。于是,季节的每一丝颤动,都可以印刻在眼里、襟间。捕捉与寻觅,感知与领受,深味与思考,那些匆匆而过的生涯岁月,藉此便获得了抽离于粗伧与仓促的不二法门。故而,阅读唐人笔下的斑斑物候,辗转于那些月夜雨檐下的迹迹心痕,不需要更多的讲解,我们就这么和诗、和美相遇了。“人,诗意地栖居”,这句海德格尔的名言,更是在唐人的这些诗句中消解了它自身的深奥与高冷——不需要哲思奥理,此间自有幽径可通、可循、可抵。
的确,唐人诗句中的那些物候,和我们离得就是这样的近,似乎一推窗、一开门、一展卷,就满眼皆是,扑面而来。不过,如此这般的色色光景,多少也形同于梦境——总是映照着不一样的时间心境、物华人群;既陌生,又熟悉。徜徉其间,任四季流转,时空遁形,委实是别一番境遇。于是乎,身边那些看似粗伧不堪的现实,居然可以被诗意一一照亮点燃,至于那些看似苍白模糊的过往,也仿佛得到一份悄然唤醒的契机,得以在不同的世代,继续它的隽永鲜活、繁复深沉。

扫描二维码购买《唐诗物候》










